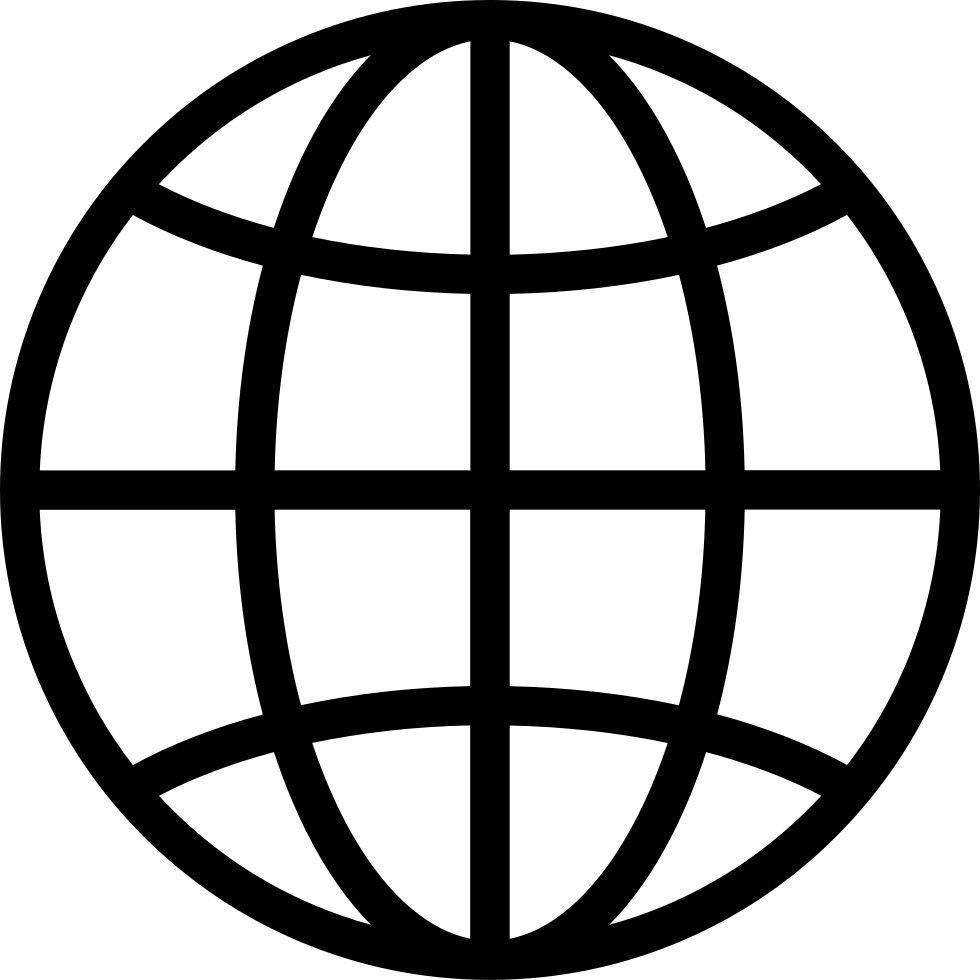08. 日本:完美强迫症的炼成,个人与集体之辩(下)
Manage episode 307267962 series 2657217
内容由看理想提供。所有播客内容(包括剧集、图形和播客描述)均由 看理想 或其播客平台合作伙伴直接上传和提供。如果您认为有人在未经您许可的情况下使用您的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您可以按照此处概述的流程进行操作https://zh.player.fm/legal。
收听提示
1. 在日本,校园霸凌是如何发生的?
2. 父亲应该如何参与育儿?
3. 为什么要让孩子光脚踩泥巴?
本期嘉宾
高益民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在三联中读开设《智慧父母慢教养手册》课程。
梁文道
“看理想”策划人,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主讲人。
正文
周轶君:欢迎回来,我是周轶君。这一集我们继续聊上集话题。上集我们说到日本教育当中,是既保护孩子的天性,又教育他们尊重规则、服从集体的。然后就有观众问了,既然日本的儿童教育那么好,为什么长大以后一个个都觉得好像很压抑,在公司里面也很压抑,自杀率又很高,这个问题怎么破?其实到底是有关联吗?
高益民:可能有关联,其实我觉得任何一种教育或者任何一种文化,它都一定有它的问题。因为日本这种精细化达到了一个很……
梁文道:非人的地步。
高益民:我觉得有时候其他很多民族,不光是我们很难模仿,就是其它很多国家民族都很难模仿,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其实在实践当中或多或少肯定会对个性是有影响的。你比如说他们可能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相对来讲是比较开放、比较自由的。但是到了中学以后,中学开始更强烈地去模仿成人社会这种等级观念,集体的这种观念,所以他的前辈后辈的欺负就很厉害了,到了中学以后就变得很厉害。
周轶君:那他们自己有这个反思吗?为什么儿童的时候可以放任他的天性,到中学阶段忽然就变成了对成人世界的这种模仿。
高益民:他们有他们的反思,我看您那个片子里也有老师谈到这一点了。
梁文道:是,霸凌。
高益民:其实他们这个霸陵跟集体是有关系的,他们的霸凌经常出现在集体对个人上面,不是说比如说我身强力壮来欺负你,一对一的这么欺负,经常是一个班的人来欺负不合群的一个,觉得他不是我们的(一员),你看我们大家说的事他也不遵守,我们的规则他也不认同。
梁文道:他是个坏人或怎么样。
高益民:当然我们中国也存在,就是很怕转学转不好对孩子出现这种影响。
周轶君:所以他们这个集体教育里面有好的东西,但是消极的那一部分它其实也蛮难剥离掉。
高益民:很难完全剥离。
周轶君:所以也有观众会问一个问题,刚才您说到转学的问题,就是日本有学区房吗?日本他们的家长在择校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要到哪去买房子,要去哪个学校,也这样很焦虑吗?
高益民:也会有,实际上这个是任何国家都有。
周轶君:芬兰没有,芬兰我问他们,他们说没有学区房,但是近几年有一些台湾的妈妈去了以后,开始有学区房这个事。
梁文道:把这个观念带过去了。
周轶君:有人这样讲,但还是比较少见。
高益民:日本总的来说它的社会阶层分化还不是特别严重。
梁文道:教育资源也算平均。
高益民:最关键的是他有一个想法,就是生源一样不一样跟我教育没关系,我要对他们提供同等的教育,公立学校要对不同人群提供同等的教育。
周轶君:它在今年10月份还开始了所有的学校是免费入学。
梁文道:幼儿园。
周轶君:是,对,幼儿园,那就没有公立私立之分了吗?
高益民:当然也不可能一下子来改变这个情况,因为它好像还有一个过渡,就是根据你收入的。
梁文道:是。
高益民:家庭收入的多少来过渡。我说的是可能是小学以上,就公立学校这个系统,那么公立学校系统原则上是给你提供大致差不多的教育。如果你觉得不满足,你可以到校外去,可以上补习班。
周轶君:他们上补习班的情况普遍吗?因为我看到有一篇文章特别有意思,他就驳斥我拍的日本,他说不要以为日本的学校有多好,我很庆幸我的孩子在中国念小学,他说因为对于日本的家庭主妇来说,去超市买一片西瓜都很贵,说送孩子上几个补习班,那都是富人阶层的事情,哪像我们,我可以给孩子上十个补习班。但在日本他们也上很多补习班吗?
高益民:难道上我们国家补习班不需要钱吗?
周轶君:他说就相对便宜。
高益民:日本的补习班也很厉害,可能跟东方的这个特点。
梁文道:对,没错,尤其是为了考大学的那种补习班。
周轶君:他们都补什么呢,是补学科还是说有什么音乐舞蹈这些?
梁文道:不,补考试就是。
周轶君:就是补考试?
高益民:补考试的是非常多的,当然跟我们一样,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兴趣的也要多一些,但是到了往上走,越往上走补考试的越来越明显。
周轶君:升学压力大吗?比如说也是不是有高考,然后大家都要拼这样子。
高益民:升学压力我觉得永远是很大的,因为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实在日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上大学。
梁文道:没错,因为人口老化的关系。
高益民:少子化,孩子就是学龄学生在减少,学校还是很多。现在问题是学校要倒闭了,因为没人上。
梁文道:反而学校想办法吸引学生。
高益民:但是好学校永远是少的。
梁文道:对,你像东大这种。
高益民:对。
周轶君:竞争还是比较激烈。
梁文道:我有一些朋友在日本教书,他们那个大学还不错,但是他们告诉我说,他们那个大学主要用来吸引学生的卖点是什么,是我们这个学校就在青山,Oyama,这是个多时尚的地方。然后很多孩子去那儿上学就等于天天去三里屯,去国贸,去工体差不多,就那种感觉,就觉得好爽,一个学校用这个当卖点,真的是少子化到这个程度。
周轶君: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看到,我就发现在日本每一个人,其实说每一类人你在社会上都有个角色,这个好像跟他们的集团主义也是有关系,比如说我要是一个家庭主妇,那么我的角色很多时候我就是要陪伴孩子。在日本如果你是出去工作,甚至说工作占用你很多时间的话,这个似乎是是比较少见的。当时不是有一个女议员去开会的时候带着孩子去嘛,就被大家赶出去了。
梁文道:很离谱。
周轶君:对,但是它也有一个反过来说,社会也会照顾到你这种需求,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没拍到的是什么,他们有夜间的托儿所。如果爸爸妈妈我们讲叫双职工,你都得上夜班,那我就得给你的孩子安排说你的孩子去哪儿。
既然社会上有这个工种,两个人夜里都要去工作,那孩子就要给夜间的这种托儿所去。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接触过这个,在新宿都有。那他们的,比如说妇女在他们的教育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有的中国妈妈看了就觉得日本妈妈特别辛苦,因为好像你必须呆在家里做很多事情。
梁文道:便当要弄好。
周轶君:各种各样的事情,好像她自我的那种角色就比较少。
高益民:因为传统上是女性是在家里相夫教子的,所以确实大量的女性她就选择,特别是生了孩子以后,她就呆在家里。但是这个情况也在改变,因为日本整个社会的状况在改变,就是男女平等的意识也在逐步增强,所以实际上现在的工作女性要比以前多不少。
周轶君:我最近看到有一个日本的征婚广告,男性都要征集独立女性,原来他们也有这种转变。
高益民:也在发生变化,但是由于有这个传统观念嘛,所以社会对女性可能有一种传统的眼光。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女性,如果你不能照顾好孩子,你不能做孩子喜欢吃的饭菜,可能大家指指点点。这个我觉得还是。
周轶君:是吗,还有指指点点?
高益民:会有的。
梁文道:会有的。
高益民:因为家庭主妇没事,主要的工作就是指指点点。
梁文道:没错。
周轶君:我听说在日本好像近年有一个电视剧就更夸张,说是比如说在这个妈妈会里面,比如说你几个都是这个学校的妈妈,也会根据丈夫的工作职位分出高低来,而且这会影响到孩子,孩子都会有,有的孩子如果他的爸爸是没有做到什么社长科长他就会比较觉得自己是低人一等。
说有一个妈妈在妈妈会里面她总是,丈夫职位高的妈妈会指挥她去买东西、订餐厅,干嘛干嘛,老是对她去指挥,最后导致这个妈妈就自杀了,就在那个电视剧里面,那我想它也一定是反映了某种社会状况。
高益民:我想一定会有这种状况。我在日本的时候去开家长会,只有我一个人是男性,其他除了我以外,班里所有的家长都是妈妈,没有父亲去参加家长会的这种情况,那么她们之间就有很多的叽叽喳喳的那些东西。
梁文道:对,很多讲究。
周轶君:那中国现在其实很多人也问这个问题,就是爸爸去哪儿了,就是很多时候是妈妈在承担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有的观众听众也会问,如果是由妈妈来抚养孩子,就主要的精力,那会不会有所缺失,或者说爸爸应该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高益民:肯定有所缺失,所以日本的教育学家、社会学家都提出有一个现象叫父亲不在,就是父亲不在。就是在整个家庭教育当中,父亲一早上就走了,晚上孩子睡觉以后才回来,所以跟孩子接触很少,这也是日本家庭教育当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
周轶君:他们怎么解决呢?
高益民:所以现在你看到日本从政府也好,就开始提倡让男性也参与到家庭教育里头来,包括休产假的过程当中给予男性的一些方便。
梁文道:我觉得他们也在改变。
高益民:也在改变。
周轶君:还有一个小细节,当时我们拍摄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后来看片子有一个懂日语的朋友跟我讲,他说当时拍莲花幼儿园的时候,他们的副校长他每天会在门口去迎接那些孩子嘛,他是这个校长,那个孩子很小读幼儿园的,他跟孩子会问好,而且他用的问好的词是日语的敬语,就是等于说您好那种意思。他们对孩子是不是尊重到这种地步,包括说他们这种师生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高益民:因为他要给孩子做榜样嘛。
周轶君:他是教孩子怎么跟别人打交道。
高益民:对,还不完全是尊重。
周轶君:这样子啊,但是他们的老师据说对孩子,特别幼儿园的孩子他是会非常的了解,说他们毕业季的时候就很有特色,说校长会念出每一个孩子他们干了些什么个性等等,说经常父母听了就哭成一团,是有这样吗?
高益民:我个人没有经历,因为我们就读了10个月我们就走了,个人没有这个经历,但是我们现在国内的一些学校幼儿园确实很下功夫在这方面。因为我去过一些学校,就是很有心的校长他也会做这些工作,比如说北京有一所学校,它会让你留下每个孩子的手印。
有的学校,我讲的这个学校就是北京的一所学校,这个校长而且是个男校长,他非常有心,孩子的小学录取通知书不是发了嘛,他一年级入学以后他又给收回来,为什么收回来呢?他让老师们每一年都写一句话给孩子留在上面,就是这一年你有什么进步,你有什么表现,到了六年毕业的时候,再把这个小学的入学通知书在毕业典礼上再发给你,也确实有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他们花很多心思在这方面。
周轶君:是不是来自于老师的鼓励是特别重要,而且是对个人的个体的这种。
梁文道:那肯定的,那肯定,因为孩子跟,你想想看,除了家长之外,他接触的陌生人其实都在学校里面,他跟社会第一步接触的那个步骤就在学校里面。所以学校里面他的同学,尤其老师怎么对待他,是他人生过程中第一次体会到人家跟他的互动是怎么样的,他是不是得到尊重,有没有被爱护,都在这个环节里面。
周轶君:那大家也很好奇想问,请教高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您一直研究日本的教育,也有比较教育的研究,那有什么是可以从中,我们的教育可以去吸取的吗,就说您这个研究有没有直接用于我们的教育的?
高益民:实际上直接的移植是非常困难的。
周轶君:当然。
高益民:即使我们有时候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在第一线,我们国家第一线老师对日本的教育还是越来越感兴趣。因为他们发现日本的很多做法,我们可以吸收进来,比如说有的小学跟我讲,他说听你说日本的小学分班,每年都要重新分一遍。
周轶君:有的学校有这样做,我有经历过。
梁文道:对。
高益民:他一年级升二年级就重新分一遍,二年级到三年级时候还要重新分一遍,一直到六年级,所有的同学跟所有的同学都曾经是同班同学。他说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如果在学校规模不是特别大,班额比较小的情况下,其实他这样把它打通了。
梁文道:让他们认识的人多了。
高益民:对。
梁文道:所以你常常看到他们每年要升学的时候,就会公布一个班级分班表,要全部小孩挤在那边看,今年我还在这班,今年你又跟我坐在一起。
周轶君:还有一个他有时候会分到说这个老师我喜欢或不喜欢,或者说这个朋友我的同学我喜欢或不喜欢,是不由他选择,他总是在接触一个新的环境,因为现实生活就是这样,你不能总遇到你喜欢的人。
高益民:对,所以他们的老师要求也要换,一般不会有一个老师从一年级跟到六年级,因为一个老师他要教所有的课,如果你一个老师还要跟好几年的话,如果有不喜欢的学生,那就很麻烦,所以他一般一年一定要换一个老师。
高益民:当然这些是技术上的一些做法,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地方。还有一些大的方面,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可以参考,你比如说他们对自然的这种感受,特别注重在对自然的这种体验。我看到您那个片子里拍到,你看那个幼儿园里头所有的泥土的操场。
梁文道:藤幼儿园那个。
高益民:都是光脚的。
梁文道:对。
高益民:他让孩子去体会。
梁文道:莲花幼儿园那个。
周轶君:说到这个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我的片子最大的贡献,很多家长告诉我他们脱了孩子的袜子和鞋子,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光脚对大脑发育好,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都光着。后来他们说有的是什么呢?就是年轻的父母,他们早就想给孩子脱掉了,但是爷爷奶奶不愿意,然后他们把这个片子给爷爷奶奶看,就直观的告诉你,外国的小孩也光脚跑,他们就同意了。
高益民:对,他们就是让孩子感受到四季的变化,感受到动物,你看那个幼儿园的园长拿水龙头。
梁文道:撒小孩玩。
高益民:撒小孩,这个在日本确实挺常见的。
周轶君:常见的?
高益民:对,有些幼儿园,我去的一个幼儿园他们干脆就跟家长说好,你一天就穿一身带一身,为什么?因为这孩子。
梁文道:回学校一定弄脏。
高益民:对,一会定弄脏,而且他们会连泥带水的在玩,所以学校会安排他们换好衣服的,这些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可以参考的。
梁文道:挺好的,其实小孩都很高兴。
周轶君:对,很多人说那家长会去告学校的。我们这边也说到了一些听众的问题,大家有一些非常感兴趣的。那学区房的事情,我刚才已经问过了,其他的就是他们会认为说现在说挫折教育还是说鼓励型教育,您觉得哪一个更好一些?因为在日本似乎是对他们比较严厉。但是也有的学校是鼓励型,他们觉得到底哪一种方式更适合中国的孩子呢?
梁文道:我不觉得这是那么断然二分嘛。
周轶君:一个非此即彼的事情。
梁文道:对呀,这个讲法好奇怪,我觉得。
高益民:对,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么一种思维方式,我觉得需要客服。你比如说关于愉快教育、快乐学习,就打得不可开交,有的人说我坚决反对快乐教育,能不吃苦嘛,学习能不吃苦嘛,好像吃了苦就不快乐似的,是吧?那痛并快乐着是一种什么情绪啊,什么感受啊,是吧?其实都是相互交织的。
梁文道:对。
周轶君:我倒觉得这个有可能会产生这种想法是挺自然的,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跟可能过去的历史上的中国父母都不一样,我们经历的这种社会的变化,一下子好多价值观冲击进来,有时候你确实想,我们以前是错的,对孩子比如说打骂教育,那我要放养到什么程度算好呢。
他确实会产生这个疑问,一定是有的。包括这边有的就问到一个问题是跟日本有一点点关系的,他说我们比如说鼓励孩子,你要有自信,有独立的思维,对吧?那他以后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怎么办,如何让他在大环境下坚持自己的原则,这好像跟刚才那个一样。
周轶君:也是非此即彼吗?
梁文道: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自己做节目也常遇到这种问题,就我们好像你一独立思考,你就没办法进入社会,一进入社会你这个人的大脑就完了,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来想事情呢?我觉得日本那个经验恰恰好,就包括你拍的这一集就看到。
周轶君:那个度。
梁文道:对,而且它的这种集体性是在于充分考虑到其他人的前提下的自我的成长跟自律,其实一个人的独立思考就包含了你有没有办法去平衡的考虑其他人的观点。
高益民:对,您记不记得那个片子里园长用了一个词叫共振。
梁文道:对。是。
周轶君:他说得非常好。
高益民:就像我们比如说唱合唱一样,正因为你唱你的声部,我唱我的声部,我们声部都不一样,最后那个和声才是最美的。
梁文道:是。
高益民: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唱一个调子才是最美的,对吧?
周轶君:但有一个挺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当时没有拍到的一个东西,我们也有那个素材但是没有办法用,它是什么呢?有一个来自于,我忘记是哪里,就是中国孩子的代表团到日本学校去交流,大家相处了三天吧,最后有一个好像汇报演出一样,大家来表演节目。日本那边出了三个节目,全部是集体表演,就是大家一起唱歌,大家一起玩乐器,他唱歌是高低声部的那种唱法。中国这边出的全都是个人演奏,就是全部是以我个人的技巧。
梁文道:就全班表演最厉害的三个人。
周轶君:对,基本上是这样。
梁文道:基本上是这样。
周轶君:这个也反映了我们,我觉得就很难讲,咱们不是说比较谁好谁不好,但是你会看到明显我们对于一种什么叫成功的教育或者卓越等等的理解跟日本不一样,我们特别在意一个个人的成功,这个其实也导致了很多后来家长做出的选择。
高益民:确实是因为我们国家,因为可能相对于人口而言资源的不足,或者非常优质的这种资源不足,也可能是由于我们现在独生子女的影响,总而言之我们个人跟个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惨烈,在教育上也是这样。所以有一次我到一个学校去开家长会,开家长座谈会,去了解他们对于这个学校的看法,结果发现这些家长都把孩子送到很多课外班。
那么送到课外班以后,家长就有不同的意见,一部分家长就认为我们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课外班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学校的教育质量不行。你讲得不如海淀,你们教育的不如海淀教育好,所以我们放学以后才要把孩子送到海淀去接受课外教育。所以你们学校就应该把这个知识教育好好做好,结果说完了之后大家都很赞成,说这个意见非常好,我们要求加快进度,加大难度是吧?
结果有一个家长我觉得说得挺有意思,他说大家不要提这种意见,因为无论加大到什么程度,我儿子还是要跟你儿子比,如果这个学校把难度加大了,也加快了,我还是要把你给比下去,我为了把你给比下去,我还得上课外班。
梁文道:说得很有道理。
周轶君:这个好难破,2018年中国K12课外培训市场规模是5205亿元,我在英国看到过这个情况,有一个报道讲英国的补课教育,这个规模也是一个20亿英镑的市场,但是不一样的是,它补学科的数理化这些的,主要是中国和中东家庭,英国人家庭主要是补音乐绘画等等这种艺术课。这种补课的恐慌,其实我也听到了很多,您觉得就是这种是由于相互比较产生的吗?
高益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因为所有的我们的议论,比如说差一分或者差半分,就会差出一操场的人的时候,你讲的实际上就是要挤到前面去了。
周轶君:甚至有些恐慌是不是?我也不敢说是不是有点人为造成,他会说哪个补课老师是来自于某个学校的超前班的,那么如果我去补他的课,就有可能进入那个超前班,都有这样的,补课市场都是细分到非常精密的程度。
高益民:前些年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他设置各种各样的条件,说你来参加补习了的话,我甚至可以能够帮你联系到,有一个通道,但这几年因为政策收得非常紧,实际上这个是不大存在,我觉得还是希望孩子赶到前面去。
梁文道:不过这个也跟我们整个高等教育的资源分布是有关的,大家为什么要抢一分之间的那么多的距离?比如说一分之差能够差几百人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高等教育资源其实是很集中的,比如说你在北京,比如说北大清华上海复旦,那这些跟后面一点的学校其实已经有点距离了,但后面的学校跟再后面又有很大距离。
当然全世界每个地方都会有最好的所谓的顶尖的精英学校,可是问题是人家的精英学校跟所谓的好一点的大学,就非顶级精英之间,有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呢很难讲,比如说大家今天很多人去美国留学,你说哈佛是不是名校?
那当然是,那你说哈佛跟一个公立大学,比如说威斯康辛或者加州大学的分别有大到那个程度吗?那倒好像不一定;又比如说像德国就更难讲,德国没有所谓顶尖大学,德国是完全分散开的;北欧也是这样。
周轶君:我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当时在英国去留学的时候,一个英国前驻中国大使,自己说了一个事情,他说当时有一个某贪污高官了,后来被发现了,给他打电话,说我的孩子现在在哈罗,他说我发现了伊顿比哈罗好,你能不能把我的孩子从哈啰调到伊顿,就连这个都要比,他就说对不起,我们在英国不是这样做事情的,那个大使跟他讲,就是这种差别,这种比较。
高益民:实际上日本的高等教育也是有这种类似的问题,比如东大呀京都大学,私立大学里头的,庆应啊。它的等级序列性确实比较强,所以造成了这个大家都想排到前面去,所以美国最早的,它的一个经验就是要办州立大学,州立大学就是每个州至少有一所比较好的大学,大家就不用再去追求那个顶尖了。
另外州立大学离家乡比较近,它的各方面的支出也比较少,所以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之后,美国就对日本提出这么一个要求,一个意见吧,就说你们要学习我们美国的这种平等的这种精神,你每个县都应该办一所县立的大学,但是日本后来把这个意见稍稍作了一些改动,就是每一个县就办一所国立大学,这样来保证地方的老百姓,有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
但是问题是它战前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个序列,帝大序列,现在没办法来改变。
周轶君:他怎么来保证这些国立大学或者州立大学的学校的质量是好的呢?而且是大家认可的好。
高益民:当然美国它是有一套系统,这个系统它就是通过一个外在的评估系统,我们叫认证系统,这个认证由各个大学来组成一个认证的协会,这个协会来对每个学校进行评价,如果在我这个系统里你评价很糟糕的话,那么你以后招生就会很困难。它通过这个他有一套质量保证。
周轶君:这个评估的结果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吗?
高益民:对。
周轶君:噢,是这样,还有人问为什么大家一谈到日本的教育,大家就说好可怕,对于细细节的这种,比如他们很准时,他们很完美,说日本人正在布局未来好可怕,为什么日本教育让中国观众感到可怕呢?您觉得可怕吗?
高益民:有那么可怕吗?
梁文道:我觉得中国教育也很可怕。
高益民:因为日本有些方面做的确实到了极致了,确实也很难模仿,不容易模仿,至少可以说这样,比如说他这个垃圾分类,分类过度也是一种社会浪费,可以这么说。但是日本它确实做到了,其实我们中国过去也有个词叫敬畏,当你觉得他做得很好,你有敬的成分就有畏的成分。
周轶君:确实是,还有一个问题也挺有意思,可能又反映了我们说的这种非此即彼的这个想法,看来是很普遍,这两个问题可以放在一起,我觉得他们是相互自证了吧,一位问作为妈妈是否可以更关注自己的生活,这样在其他人看来是否会太自私了?
第二个问题说,全职妈妈很受歧视,尤其来自于同性的歧视,仿佛选择全职,就是脱节偷懒,甚至low,我该怎么应对?哎呀似乎这个问题是不是该由我来回答这样,我的感觉,我说句心里话,我觉得你要养育好一个孩子,真的是要有一个全职妈妈,我说要养育好,真的你如果每一个,我们所有读到的关于教育的这些要求观念经验,你都要做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全职工作。
梁文道:或者全职爸爸。
周轶君:对,一定是要有人是全职去做的,甚至还多于一个人。那对于我来说,比如说我没有做一个全职妈妈,很多时候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有的时候也很想花更多的时间去陪孩子,但你有时候你做不到,这里面有有很多的原因,不光是你要不要挣钱,你要不要完成个人的野心或者等等。
它的原因太多了,我就觉得说每个人你可能你能够做到多少做到多少,而且可能还有一点,你跟孩子的不光是一个你对他的陪伴和直接的教育,而是你自己做成什么样子,对孩子可能是会有影响。
梁文道:不过这个我倒觉得我们可以拉远一点来看,说全职妈妈或者全职爸爸是否必要这件事情,这个问题现在变得尤其严重,是因为我们现在家庭太单元化,现在大部分家庭都已经是核心家庭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就只有一个父母,带着一个到两个小孩,现在可以开始,那你,谁出去工作,谁在家带着小孩。
那以前的家庭比较单元比较大的时候,其实你会注意到对孩子的教育抚养照顾看管,是一个家族内部其他所有长辈可以共同参与的事情,现在比较矛盾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一方面所有的家庭是核心化, 就两代人,然后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又预期男女都应该出去工作,以前的话反而不是,以前一家人里面有很多人。
我觉得在观念上反而中国现在面对更大的麻烦,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认为我们家的小孩轮不到人家管。这个我觉得就跟我们刚才讲的日本有点不太一样,日本你会注意到,有时候在一些街坊在一些邻里,这个孩子是被大家一起教训的可以,我看到邻居或者别的亲戚也会指责你,如果做的不对或怎么样,他会觉得这个是小孩,比如说几岁幼儿园这种,大家都可以来管一管教一教的。
但是在中国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比如说你会觉得人家的小孩我们别管那么多事,或者人家跟你说小孩怎么那么吵,关你屁事啊,我们比较容易这样是不是?所以变得很矛盾,我们的小孩等于只剩下只能直接面对父母了,因为很多现在的原子化的家庭,他爷爷奶奶见不到,更别说他的舅妈姑妈姑丈这都见不到,没有别的亲戚,他就只有一个父母,然后这时候父母又都要上班,那这时候这种问题就会出现了。
周轶君:还有一个是专门给高老师的问题,她说她是一名河南籍,在职将近10年的特岗教师,河南是一个高考大省,那么特岗教师的确极大的补充了地方的师资, 改善了农村教育的质量。那么她自己是想考研究生就是研究教育,想请问她也想读比较教育学的研究生,她问学术研究可以促进目前教育的不均衡,教育制度中的种种的改善吗?
高益民:教育研究它所起的作用是长期的,缓慢的,它不可能直接去改变实践,也不可能立刻影响政策,因为它这些研究,这个人类对事物的认知总是一步一步地前进是吧?
那么做比较教育研究也好,做其他教育的研究,幼儿教育的研究,他写出的做的大量的调查和这个论文能够被政策方所认知,能够被第一线的老师,还有学生和学生家长所认知,那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想通过比如说研究来立刻改变现实。我觉得是比较不现实的,所以要有一个长期的。
周轶君:我听高老师今天讲的,我觉得最感触深的就是日本学习了人家很多东西,在教育上也一样,但是就怎么学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对吧?是整体的学还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学,你学什么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两位,也感谢您的收听,有什么问题欢迎在节目的留言区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再见。
24集单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