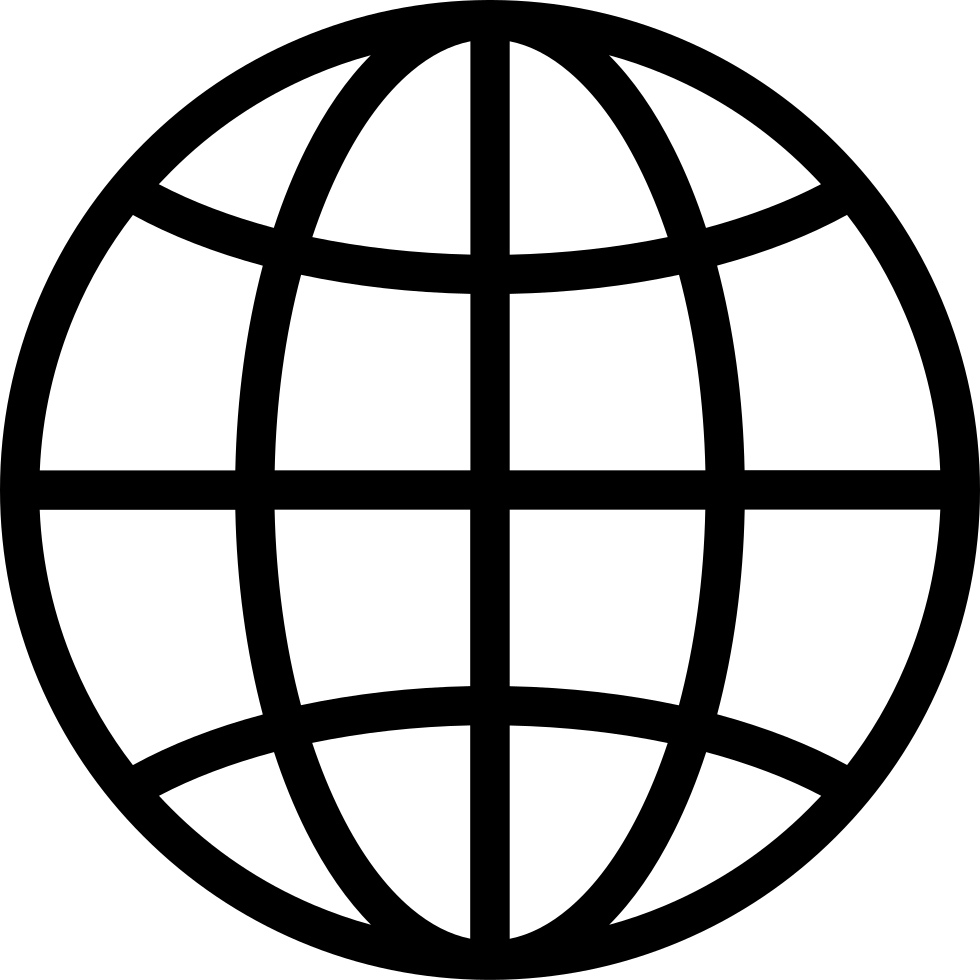Episode 34: 职人与素人——记 P.S.F. 生悦住英夫悼念演出
Manage episode 268001340 series 1540280
(本期內容是 2017 年 6 月 28 日《無次元》会员通讯免费试读。)
演出已经进行了超过一半,「迷幻速度怪胎」(Psychedelic Speed Freaks)还没有现身。我们听到了可爱的手风琴即兴、冷淡如水的钢琴小调、热闹的伪业余集体唱咏、灯光全关的 acousmatic 循环长音、阿部薰风格的萨克斯管独奏,但就是没有 P.S.F. 闻名于世的高速迷幻爆音。
现在妳终于开始真正理解 P.S.F. 和生悦住英夫(1949–2017)了。
二零一七年六月廿五日,一众乐手在马头将器的号召下,在东京六本木的 Super Deluxe 为已故的 P.S.F. 唱片公司老板生悦住英夫举办了六个小时的纪念演出(乐队名单见文末)。
生悦住英夫是过去三十多年东京地下音乐圈绕不开的名字。他主要做了三件事:开办名为 Modern Music 的唱片店,编辑出版《G-Modern》杂志,创办唱片厂牌 P.S.F.(即 Psychedelic Speed Freaks 的简称,取自 High Rise 乐队一九八四年的专辑名)。杂志是日文,唱片店在东京,从传播性上说 P.S.F. 完胜。因此他最为人知的,就是那超过二百三十种的唱片出品。从八十年代末开始,P.S.F. 逐渐受到海外实验音乐界的注意。旗下的灰野敬二、不失者、High Rise 等等也渐渐成为具有国际声誉的音乐家,在中国亦不乏拥趸。
生悦住先生去世后,许多悼念文章都提到了他在选品上的不妥协,即,P.S.F. 选择艺人的唯一标准就是生悦住本人是否喜欢。这虽然可以解释为什么 P.S.F. 旗下有那么多风格各异的艺术家,但无法解释他内心的这个标准究竟是什么,而且还可能让人误以为那标准并不存在,一切全看心情。生悦住英夫当然不是「Spotify 式聆听」的先驱。事实上,他以行动倡导的聆听哲学恰恰是 Spotify 所谓「根据当下心情推荐歌曲」的对立面。
如果要给 P.S.F. 贴标签的话,很多人想到的大概是「迷幻」「前卫」「实验」「地下」「黑暗」「即兴」等等。更了解 P.S.F. 的人会说 P.S.F. 拒绝被贴标签。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共性的团体并不成其为团体。尽管许多在 P.S.F. 出过唱片的音乐家都不认为彼此之间有什么一以贯之的风格,但这不等于说她们在精神层面没有相通之处。六月廿五日晚的十三组乐队里,Maher shalal hash baz 和 Ché-SHIZU最完美地呈现了这种精神。
从网上搜寻这两支乐队的信息,妳会知道 Ché-SHIZU 的主脑向井千惠主要的乐器是二胡,有时也负责人声和钢琴。她们的演出属于「即兴/民谣」。妳也会查到 Maher shalal hash baz 主脑工藤冬里曾经加入日本某政党,后来成了耶和华见证人的一员,此外还是陶艺师。这是很好的谈资,但无法帮助妳理解她们的艺术。
在懵懂的观察者看来,当晚的 Maher shalal hash baz 就像一支大学业余乐队或社区乐队,而 Ché-SHIZU 则像是四名智障人士的组合。前者演出时舞台上至少站了十三人,使用的乐器包括黑管、巴松管、小号、手风琴、口风琴、大提琴、吉他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几个貌似从观众席中临时拉来的路人(她们的确有拉观众上台的习惯)。工藤冬里本人穿着朴素到不适合上台的黑 t-shirt 和长裤,留着说不上发型的发型,像街坊乐队指挥一样背对观众站在舞台前方。每组艺人上台前,主持人 Alan Cummings(《The Wire》杂志作者,英文世界的日本地下音乐专家)都会用日英双语作简单介绍,乐手在调音完毕后也都会以眼神向他示意,告知「可以开始介绍了」。Maher 是唯一的例外。或许是台上人站得太多挡住了视线,工藤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 Cummings 的存在。好不容易让各乐手七零八落地调好了音准之后,他没有任何宣示地径自开始拍手击打节奏,并邀请那些没拿乐器的路人加入。正如妳会对一支社区乐队所期待的那样,路人们打出的节奏一开始并不合乎要求。于是工藤和她们反复调整,快一点,再慢一点。紧接着,乐器部就加入了。
虽然这十来号人确实站在舞台上,但这种没有开始的开始比那些喜欢走到观众区演奏的音乐家更有效地取消了舞台和观众席的界限。Maher shalal hash baz 对权力关系的消解是全方位的:指挥那土得不像话、毫无 charisma 的造型,乐手盯着乐谱看时那缺乏自信的眼神,乱七八糟的排位,以及路人们松垮的站姿,一切都让人觉得这是一场彩排,而非正式演出。主张「消费者权益」的文化消费者要怒了。专业精神何在。这可是日本,还我钱来!
只要妳继续听下去,就会发现虽然这的确不是高完成度的乐队,但也绝非一团浆糊。音乐是简单的旋律形在反复,工藤一边维持着整体的节奏,一边偶尔扫两下手中的吉他。拍手的几名路人突然开始念唱「生悦住先生」几个字(ikeezumi-san),人声从管乐与弦乐的合奏中清晰地穿插出来。掌击的节奏和反复的念诵让音乐产生了直接的宗教感。它像是招魂仪式,但却没有丝毫阴郁或沉重感,倒是大学乐团/社区乐团的欢乐氛围挥之不去。我想起朋友不久前发来 Paul Winter 在纽约圣约翰大教堂的演出海报,在我表达了羡慕之后,她说:「啊是吗?是一个有名的人吗?天哪我听完了都以为是社区音乐会……」要怎样来回答 Paul Winter 算不算有名这个问题呢?在 ECM 和 Oregon 的听众心中他当然是一个见到会两眼放光的名字,但和大部分一九七零年代的名家一样,并不属于唱片公司在可见的未来会考虑重新发行的作品。而我十分相信对 Winter 本人而言,被视为「社区乐队」绝不是一件落魄的事,正如 Steve Wozniak 不会以去中学教电脑为耻。正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我要去听一支社区乐队演奏」,而是「如果社区乐队都有高水准,这样的世界不会更好吗?」
看着 Maher shalal hash baz 在台上演出,我脑中反复出现 heuristic 一词。作为一种教学手法,heuristic(启发法)强调学习者的自我探索和试错精神,主张对不完美的方案保持开放。几乎所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音乐都是对 heuristic 的实践。如果把 P.S.F. 三十多年来的出品放到其各自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它们大部分的确拥有一种毫不理会当下音乐潮流的任性,以及技术层面的业余感。举例而言,为什么 High Rise 总是要把录音电平开到破音的程度?在他们成立的一九八零年代初,时代最强音是时尚的新浪漫和阴郁的后朋克。而且,他们不知道这在音响工程上是错的吗?难道没有在保证不破音的前提下追求大音量的可能吗?当我们听到灰野敬二说自己演奏那么多乐器是为了提炼出它们「本来的声音」,因此恰恰不能去学习每种乐器的正确演奏方式时,有没有想过 Stephan Micus 在做同样的事,而且远比灰野做得更好?只有当妳意识到这位 P.S.F. 的台柱艺术家在其自己宣称的实践范畴内只是二流水平、并且与这一事实和解之后,才能对这个独特的日本地下音乐小宇宙形成更确切的理解:P.S.F. 是一种素人艺术(art brut)。
所谓素人艺术,简单说就是并非职业艺术家做的艺术。但它有一个狭义特指,那就是精神病人做的艺术。(东京车站画廊刚刚展出过的 Adolf Wölfli 就是一位典型的素人艺术家。)精神病人和艺术家这两种身份有各种层面上的关联,但我们在这里指的是性格或精神上多少偏离常轨,且没有受过正式艺术训练的人所进行的艺术实践。尽管这一定义与社会关于艺术家的刻板印象高度重合,但如今符合这一定义,同时又在较大的范围内被承认为艺术家的人越来越少。作为教育体制化的一种表现,知名艺术家越来越多地出自「对口」的知名艺术院校,而非野生民间。虽然很多人或许都有幸认识一两个私下能做出很不错的作品的非艺术家朋友,但当我们去参与艺术鉴赏实践——听音乐会、看画展、看戏剧——时,见到的往往都是在身份、训练和意识上都符合「专业标准」的艺术家。P.S.F. 是一个例外。它在日本实验音乐史上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它旗下的艺术家却多少都有一种意识上和实质上的业余感。在这里,实质上的业余感更加重要。有相当多的非学院派音乐家都没有受过科班训练,因此拥有意识和身份上的业余性。但随着艺术生涯的演进,很多人的声音逐步被现代工业生产体系与个人生长熟成的生物性打磨出了专业感,其身份也已和现代唱片工业体系紧密结合。P.S.F. 的艺术家则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这种制作上的业余感。她们,如同那段如今已经家喻户晓的广告文案说的那样,是「misfits, rebels, troublemakers」。她们毫无疑问是在「用不同的视角看待事物」 ,毫无疑问「不喜欢规则」,毫无疑问「对现状缺乏尊重」。但相似点到此为止。苹果从人类历史上挑出了几位天才,并通过给他们打上「疯狂」这一标签完成了对「疯狂」的贬义褒用,可是显然并非所有疯狂者皆为天才。那些并非天才但同样不喜欢规则、用不同的视角看事物的人,不仅在苹果的乌托邦里没有位置,反而很可能恰恰是被实打实地视为疯子、加以迫害的一群。一部分「疯到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的人」改变了世界,但更多这样的人只是笑柄。生悦住英夫听到了这些声音,并通过 P.S.F. /《G-Modern》将它们放大。
如果妳是素人,在缺乏专业指导的前提下妳当然只能靠 heuristic 来摸索学习。而值得提醒的是我们每个人当然生来都是素人。业余感和专业感的奇妙纠缠,在 Ché-SHIZU 的演出中得到了难以言喻的感人体现。这是一支由向井千惠牵头的四人团。她本人演奏二胡和钢琴,工藤冬里负责吉他,此外还有贝斯和鼓手各一名。音乐响起。一种古旧的中世纪质感油然而生。(注意 Paul Winter 称自己的乐团为「consort」,那是指演奏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乐团。)二胡和其它几件西洋乐器在调律上的微妙差别让音乐听起来跑了调。向井面无表情,拉琴的动作机械笨拙。而刚才指挥那群「乌合之众」的工藤仿佛一个刚学会弹吉他的大叔,带着认真的傻劲盯着乐谱,动不动不合时宜地发出一些不合拍的声响。最强悍的要数鼓手,直接把脱了鞋的左脚架到了鼓面上!和 Maher shalal hash baz 一样,这个形如草台班子的乐团奏出的声音并不马虎。有经验的听众马上就会明白那业余感是演出来的假象。早在一九七六年,向井千惠就是 Fluxus 派作曲家小杉武久主导的即兴乐团「East Bionic Symphonia」的成员,她完全有能力像当晚其她几位音乐家,例如萨克斯管手川岛诚、双人即兴吉他组合长谷川静男、或是代表性的灰野敬二 + 今井和雄那样,送上一台典型的延续自由爵士和声音艺术血脉的演出。但那样做意义何在?每周在东京都有各种各样的自由即兴音乐演出,正如每周都有各种各样的迷幻摇滚演出。和日本的所有东西一样,再前卫的音乐也会很自然地被各种「整理术」类型化,逐渐打磨到像银座的高级甜品一样让妳无话可说的高完成度。Ché-SHIZU 选择了与职人精神迥异的素人精神,但她们很难掩饰自己在音乐修为上的专业度。鼓手不停地做出各种夸张且多余的姿势,在鼓点间隙把鼓棒高举到空中。稍微不那么熟练的鼓手就会因为这种荒诞的把戏而打错节奏,而他的每一拍都滴水不漏。工藤冬里仍在继续弱智人一般的表演,有时还着急忙慌地把用来扫弦的右手伸到吉他颈部去按弦,仿佛左手手指不够用了似的。所有这些小动作都不能阻碍音乐的流畅前进。这是难得一见的景象:一支具有职人水平的乐队在假装素人。她们让自己的职人性露出了恰到好处的分量,让专业主义的信徒无话可说(「这些人是真的会玩音乐的」),同时又让负责营销的唱片公司同事大脑宕机(「这什么玩意?怎么卖啊?放到哪个类别?目标听众是谁?」)。演出进行到一半,工藤冬里、贝斯手和鼓手欢快地跳起了丑陋拙劣的舞蹈,向井千惠则从包包里拿出一袋小橡皮球用力往地板上和观众席里扔,把现场变成了一台即兴戏剧狂欢。
即便是在演出形式上,Ché-SHIZU 也把自由贯彻到了每一个细节。由于当晚演出人数众多,每组艺人的时间都有严格控制。Ché-SHIZU 一曲奏毕,向井转头向观众致谢,并用眼神示意乐队成员。就在贝斯手把效果器的电源关上,其他成员开始收拾设备时,向井却又若无其事地坐到了麦克风前!作为观众,我们很难知道这究竟是事先安排的「戏」,还是她真的临时起意打算加演一首。这时主办者马头将器从后台绕到舞台侧面,示意向井结束演出。我低头看表,的确已经超时,但向井毫不在意,对马头做出一个「再来一首就好」的手势,硬是把最后的曲子演完了。不论她是有意无意,我都把这视为向现代社会对时间的划分竖起的中指。说了开始才能开始,说了结束就必须结束,因为怕坐不到最后一班地铁就要提前离席的人们,音乐的天国不会有妳们的位置。
压轴的灰野敬二在开始表演之前,清唱了一首著名日本儿歌《滨千鸟》(一九一九,弘田龙太郎作曲,鹿岛鸣秋作词)——生悦住生前最喜欢的歌曲之一。一个出版了大量噪音和实验音乐的人会偏爱一首儿歌,在外人看来或许是件奇事,实际上却是非常适恰的选择。生悦住一生热爱日本演歌。在二零零七年六月的第廿七期《G-Modern》杂志的编者前言里,他说当今日本乐坛还在唱「真正的歌」的,只有从船村彻到灰野敬二的八人而已。(另外六人是谁没说,灰野唱「歌」的功力可以在深圳明天音乐节的这个视频里见到。)什么是真正的歌?用心演唱的歌而已。这个老生常谈的定义掩盖了关键事实:如果歌要用心来唱,那么喉咙就并不重要,换句话说,就是乐器和类型并不重要。能够用心唱歌的人,也能用心演奏吉他、钢琴、二胡、西塔琴、尺八、收音机、自制废铜烂铁、或是电冰箱。反过来说,注意力永远在 Max/MSP 和古董合成器上的人,永远不会明白什么是用心唱歌。
在朋克摇滚流行于中国地下音乐圈的那短短几年,「三个和弦打天下」成了一种标签,也是人们讥笑的对象。乐迷很快对靠姿态吃饭的乐队失去了兴趣,转而追捧更有「技术含量」的音乐。P.S.F. 的出品虽然与朋克音乐并无直接关系,但它旗下的音乐家大部分都是不会演奏音乐的素人。这是人们熟悉的陈词滥调「职人日本」之外的另一个日本。在第五十四期《Reconcilable Differences》播客里,John Siracusa 说互联网催生的一种创作形态是让缺乏某种必备技巧的人也可以以创作为生。他以 xkcd 漫画为例,说明一个缺乏绘画技巧的人也可以持续做出有品质的漫画。直到今天,我都不觉得大部分的 P.S.F. 唱片在 musicianship 上有很高的成就,有不少甚至算是失败之作。在人才辈出的日本乐坛,有很多乐手如果选择玩这些人的风格,都可以比她们做得更好。但那又如何?与很多人的认知相反,音乐天才的数量比莫扎特的时代只会更多,不会更少。这些天才不一定都会从事音乐工作,而世界也早就跨过了全部人仰望某几个天才的时代。生悦住英夫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昆乱不挡地聆听素人音乐家五彩斑斓的声音,并让一种潜在的秩序浮现在了世界实验音乐的版图上。从 Ché-SHIZU 与 Maher shalal hash baz 的演出当中,我看到了 P.S.F. 的真正灵魂。
参演乐队名单(按出场顺序排列)
38集单集